公共卫生学术热点追踪
Nature Medicine | 颠覆性发现:口腔细菌竟是肠癌“共犯”?跨越癌前病变到晚期,微生物群落上演“变脸秀”!
我们体内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它们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却也可能是疾病的“帮凶”。在所有恶性肿瘤中,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无疑是全球范围内一个严峻的挑战——它是第三大常见癌症,更是第二大致命杀手。最令人痛心的是,多数患者被诊断时已是晚期,例如IV期CRC的5年生存率仅有11%至15%,这使得早期发现和有效干预变得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肠道微生物与CRC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微小的生命,或许就藏着疾病早期预警的“密码”,有望成为无创诊断的全新生物标志物(biomarker)。然而,要真正破解这本“生命密码本”,将其转化为临床应用,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分辨率的研究来验证其准确性和普适性。
6月3日《Nature Medicine》的研究报道“Pooled analysis of 3,741 stool metagenomes from 18 cohorts for cross-stage and strain-level reproducible microbial biomarkers of colorectal cancer”,研究人员汇集了来自全球18个队列的3,741份粪便宏基因组样本,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庞大、最精细的肠道微生物数据库。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叠加,更是对CRC不同发展阶段(从早期腺瘤到晚期转移)和肿瘤不同原发位置(右侧结肠与左侧结肠)的微生物图谱进行了一次深度“画像”。
这项研究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不仅将CRC的预测准确率提升至惊人的0.85(平均曲线下面积,AUC),更首次在菌株(strain)水平上揭示了微生物与疾病进展的微妙关联。发现了19种此前未知的关键物种,以及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内部独特的基因谱系。此外,研究还发现口腔典型微生物的“非法入侵”是区分左右侧CRC的关键特征,并且像两类不起眼的共生菌——双环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其特定菌株的基因特征竟与晚期CRC紧密相关。这不仅仅是科学上的飞跃,更意味着肠道微生物有望成为未来CRC无创筛查和精准治疗的“侦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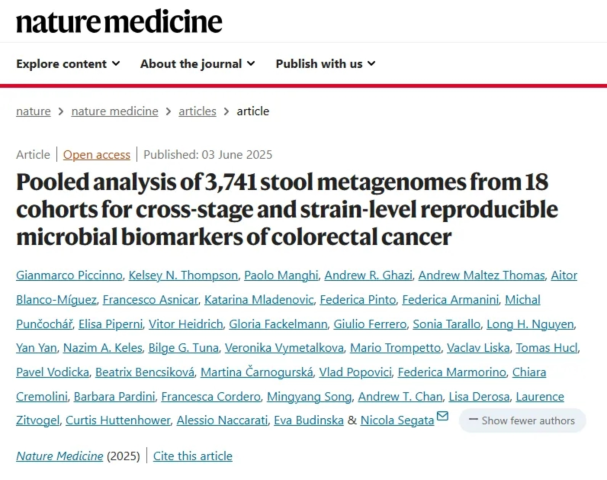
宏大视角:前所未有的“肠道联盟”大揭秘
这项研究之所以被称为“里程碑式”,首先在于它所构建的庞大且多样化的样本数据库。我们不再是去寻找单个细菌的“身份证”,而是直接把整个肠道菌群的“社区名册”给打印出来,再仔细分析每个“居民”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而这一次,研究人员汇集了来自全球18个队列的3,741份粪便宏基因组样本,其中包含12个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数据,以及研究团队新测序的6个创新队列数据。
这些样本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堆叠,更重要的是其内涵的丰富性。具体来说:
肠癌患者样本(CRC patients):共计1,471份,其中有1,191份详细记录了肿瘤的分期信息(从原位癌到晚期,如0期、I期、II期、III期、IV期),989份明确了肿瘤的原发位置(是起源于右侧结肠,还是左侧结肠及直肠)。这种精细化的数据对于理解微生物群落与肿瘤进展和部位特异性的关系至关重要。
腺瘤患者样本(adenoma patients):共计702份,腺瘤是肠癌的癌前病变,研究腺瘤阶段的微生物变化有助于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
健康对照组样本(healthy control individuals):共计1,568份,它们是构建正常肠道微生物图谱,并与疾病状态进行比较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新测序的6个队列数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肿瘤分期(cancer stage)和肿瘤原发位置(anatomic location of tumors)的详细信息。例如,队列1包含了来自欧洲“ONCOBIOME”倡议的患者数据,而队列5则来自著名的“Micro-N Nurses’ Health Study II (NHSII)”项目。这种多样化的样本来源和详尽的临床信息,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和可靠性,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地域和人群中肠癌的微生物特征。
为了从如此大规模的样本中提取出有意义的微生物信息,研究团队采用了宏基因组学技术。他们使用了MetaPhlAn 4工具,该工具能够以“种水平基因组单位”(species-level genome bins, SGBs)的超高分辨率,对微生物进行精确的识别和量化。SGBs可以进一步分为已知SGBs(kSGBs),即那些已有培养参考基因组的物种,以及未知SGBs(uSGBs),即那些尚无培养代表的物种。通过这种精细分析,研究总共检测到了3,866种细菌SGBs,15种真核生物SGBs和23种古细菌SGBs。这些SGBs中,有些物种跨越了多个SGBs,例如在结直肠癌中常被提及的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其包含了5个由MetaPhlAn 4识别出的已知和未知亚种SGBs。
除了物种组成,研究还深入挖掘了微生物的功能潜力。通过HUMAnN 3.6,研究人员生成了微生物群落的功能特征(functional profiles),包括UniRef90基因簇(UniRef90 gene families)、MetaCyc通路(MetaCyc Pathways)、酶学分类(Enzyme Commission, EC)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等信息。这使得我们不仅知道“谁在那里”,还能了解“它们在做什么”,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微生物群落与肠癌的相互作用。
此外,研究还拓展到菌株水平(strain-level)的分析。通过StrainPhlAn 4,研究团队能够评估不同菌株在肠癌表型(phenotypes)中的携带差异,并探索与肠癌相关的微生物基因(microbial genes)在亚类(subclade)中的关联。这种超高分辨率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落中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秘密。
为了探究口腔微生物在肠癌肠道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研究人员还定义了一个“口腔典型SGBs”(oral-typical SGBs)的集合。这些SGBs的定义基于一个独立的990份来自495位健康个体的口腔和粪便匹配样本数据集。具体标准是:它们在健康个体的口腔微生物群中普遍存在(流行率高于20%),但在其肠道微生物群中则相对稀少(流行率低于5%)。这项工作为后续分析口腔微生物渗入肠道(oral-to-gut infiltration)对肠癌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微生物指纹:肠癌的“秘密联络”
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多样性(diversity)和组成结构(composition)反映着宿主的健康状态。这项大规模研究首先从整体上揭示了肠癌患者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特征。
多样性与口腔菌群的“闯入”
Alpha-diversity(α多样性):这衡量的是单个样本内微生物物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研究发现,在16个队列中的9个中,肠癌患者的肠道微生物α多样性(例如Shannon指数和SGBs丰富度)高于健康对照组(标准化均差SMD > 0)。尽管这一趋势在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中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P ≥ 0.05),且微生物丰富度与临床分期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但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整体视角。
口腔-肠道微生物的渗透:代表口腔微生物渗入肠道的“口腔-肠道微生物评分”(oral-to-gut microbiome score)在肠癌患者中显著升高(标准化均差SMD = 0.47,P < 0.001)。这表明,口腔中的一些微生物可能“非法”地进入了肠道,并在肠癌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角色。这种现象在晚期肠癌患者中更为明显,评分的标准化均差为0.14(P = 0.003),提示随着疾病的进展,口腔微生物的渗透可能加剧。
肿瘤位置的影响:肿瘤的原发位置也与微生物特征相关。起源于右侧结肠(right colon)的肠癌,其微生物丰富度相对较低(标准化均差SMD = 0.25,P = 0.07),但口腔来源SGBs的丰度却显著高于起源于左侧结肠(left colon)和直肠(rectum)的肠癌(标准化均差SMD = -0.23,P = 0.003)。这进一步支持了口腔微生物在肠癌中的作用,并提示肿瘤位置可能影响这种渗透的程度。
群落组成与疾病进展
Beta-diversity(β多样性):这衡量的是不同样本之间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研究明确指出,肠癌患者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健康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方差分析PERMANOVA R² = 0.014,P ≤ 0.01),这与之前的研究发现一致。
分期与腺瘤的特殊性:令人意外的是,早期肠癌(0-III期)与晚期肠癌(III-IV期)的微生物群落组成没有显著差异(R² = 0.01,P ≥ 0.05)。同样,腺瘤患者的微生物群落与健康对照组也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 ≥ 0.05)。这可能意味着,肠道微生物群在从腺瘤向癌变过渡的阶段,以及在早期癌变之后,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而不同癌变阶段之间的微生物群落差异可能相对较小,或者需要更精细的分析才能捕捉。
总而言之,这些综合数据有力地支持了“富集的口腔微生物渗入肠道”可能是区分肠癌不同阶段和位置的关键因素。
精准预警:宏基因组学如何实现“火眼金睛”?
基于肠道微生物组的粪便宏基因组学检测,被认为是无创肠癌筛查(non-invasive CRC screening)的潜在途径。这项研究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潜力,通过利用更大的样本量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ML)算法,显著提升了肠癌病例的预测准确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机器学习模型验证策略:
数据集内交叉验证(per-dataset cross-validation, CV):在每个数据集内部进行10折交叉验证,重复20次。
数据集间训练-测试(training-testing across datasets):将数据分成不同的训练集和测试集进行交叉验证,确保模型在未见过的数据上的泛化能力。
留一法(Leave-One-Dataset-Out, LODO):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验证方法,它每次将一个数据集作为测试集,用剩余的所有数据集进行训练,从而最大限度地评估模型的普适性和稳健性。
结果令人振奋:通过LODO方法,模型对肠癌状态的预测达到了最高且最稳定的曲线下面积(AUC)。平均AUC高达0.85,范围从0.71到0.97。这相较于之前研究报道的平均AUC 0.81,有了显著提升。这表明,随着样本量的增加和分析方法的优化,基于肠道宏基因组学的肠癌预测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可靠。
更重要的是,研究还揭示了口腔来源微生物在预测中的核心地位。当模型仅使用口腔来源的SGBs进行分类时,平均AUC仍能达到0.83,而仅使用非口腔来源的SGBs时,平均AUC则为0.79。这证实了微生物群落预测肠癌的强大能力,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来源于粪便中“口腔典型菌群”的存在。相比之下,如果仅使用微生物的功能特征(functional features)进行预测,效果则相对较差,平均AUC仅为0.68至0.72。
这些结果进一步巩固了基于粪便宏基因组学的预测工具在肠癌筛查中的巨大潜力。它们不仅在大型多样化数据集上进行了训练和验证,更凸显了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肠道中口腔来源微生物存在的预测重要性。
关键物种与功能:谁是肠癌的“共犯”?
深入到微观世界,研究团队利用多队列分析的强大能力,精确识别了与肠癌相关的特定微生物生物标志物。
明星物种:不仅仅是“老熟人”,更有“新面孔”
研究共识别出125种在肠癌患者中相对丰度显著增加的SGBs(校正q值<0.1),其中包含了106种已知SGBs和19种以前未被识别的未知SGBs。同时,也有83种SGBs在健康对照组中更为丰富。这表明肠癌相关的微生物图谱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为复杂。
“老熟人”的再确认:研究再次确认了一些已知的肠癌相关微生物,如微小口杆菌(Parvimonas micra)、Morbilliform格姆氏菌(Gemella morbillorum)和口腔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stomatis),它们的标准化均差分别为0.63、0.59和0.58,进一步证明了它们在肠癌中的显著富集。
“新面孔”的涌现:更令人兴奋的是,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关联的SGBs。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个基因组上不同的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SGBs,包括SGB6007(标准化均差SMD = 0.54)、SGB6014(SMD = 0.50)、SGB6011(SMD = 0.47)、SGB6001(SMD = 0.43)和SGB6013(SMD = 0.34)。这些具核梭杆菌的亚种或菌株,如具核梭杆菌动物亚种(F. nucleatum animalis)、具核梭杆菌vincentii亚种(F. nucleatum vincentii)和具核梭杆菌多形亚种(F. nucleatum polymorphum),在肠癌中均显示出显著富集。此外,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的两个SGBs(SGB1853和SGB1855,SMD = 0.32),以及哈氏亨氏菌(Hungatella hathewayi)的两个SGBs(SGB4741和SGB4742,SMD分别为0.33和0.27),也均与肠癌显著相关(q值<0.1)。
口腔菌群的“侵略性”:在识别出的肠癌肠道生物标志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口腔典型物种。在125种与肠癌呈正相关的SGBs中,有21种(16.8%)是口腔典型物种。相比之下,在未与肠癌显著相关的488种SGBs中,只有34种(7.0%)是口腔典型物种,这在统计学上显示出显著差异(Fisher精确检验,P < 0.01)。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口腔SGBs与健康对照组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口腔来源微生物在肠癌中的特殊作用。
研究还通过重建菌株和亚种水平的系统发育关系(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发现一些口腔典型物种,如具核梭杆菌SGB6007和三种魏荣氏菌(Veillonella species),其亚类在口腔或肠道中更普遍存在。这提示这些口腔微生物可能在肠道环境中发生了基因组适应。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21种在肠癌中丰度更高的口腔SGBs的趋向性,研究利用了来自同一健康个体的牙菌斑(dental plaque)和舌背(tongue dorsum)宏基因组数据集。结果显示,有11种SGBs在牙菌斑中丰度更高(其中7种位列前8名最富集物种),而有5种SGBs在舌背中丰度更高。这暗示了形成生物膜(biofilm-forming microbes)的微生物可能在肠道肠癌微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验证这些微生物生物标志物是否与肠道中原发肿瘤的存在相关,研究评估了微生物群在区分“原位肿瘤”(in situ primary tumor)和“已切除肿瘤”(resected primary tumor)的IV期肠癌患者中的潜力。通过留一法(LODO)验证,模型取得了0.78的曲线下面积(AUC)。研究还发现,在与肠癌最相关的20种SGBs中,有13种(其中11种是口腔来源)在原发肿瘤存在时显著丰度更高。这进一步支持了“口腔共生菌渗透入肠道”的重要性,以及原发肿瘤微环境决定粪便微生物组整体特征的观点。
功能变异:微生物如何“助纣为虐”?
除了物种组成,研究还探讨了肠癌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功能特征(functional repertoire)改变。
cutC基因的关联:与之前研究一致,cutC基因在肠癌相关的宏基因组中丰度更高(肠癌对比对照组标准化均差SMD = 0.28,q = 0.001)。
代谢通路的改变:研究发现241条MetaCyc代谢通路与肠癌呈正相关(q < 0.1),而68条通路在健康对照组中更为丰富。在酶学水平,产硫酶(sulfur-producing enzymes)与肠癌显著相关,例如同型半胱氨酸脱硫酶(EC 4.4.1.2,SMD = 0.52,q < 0.001)和蛋白质二硫化物还原酶(EC 1.8.1.8,SMD = 0.41,q < 0.001),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符。
油酸(Oleate)生产的潜在作用:研究还发现两种与油酸产生相关的通路在肠癌中富集(PWY-6282,SMD = 0.4,q < 0.1;PWY-7664,SMD = 0.9,q < 0.1)。这与之前关于油酸和癌细胞增殖之间关联的假说相吻合。
氨(Ammonia)调节的微生物贡献:研究还测试了氨水平升高是否是肠癌肿瘤微环境的特征,并发现多种参与氨生产或螯合(sequestration)的通路和酶在肠癌中显著改变。特别是,L-组氨酸降解通路(L-histidine degradation pathways)在肠癌宏基因组中编码更频繁(荟萃分析SMD分别为0.41和0.32,q < 0.1)。该通路的第一步由组氨酸酶(histidase, EC 4.3.1.3)完成,它将氨基从L-组氨酸中裂解,产生尿刊酸(urocanate)和氨。这种组氨酸酶在肠癌中同样富集(SMD = 0.46,q < 0.1),在晚期肠癌(SMD = 0.18,P = 0.02)和转移性肠癌(SMD = 0.35,q < 0.1)中也观察到类似趋势。此外,另一种氨裂解酶——甲基天冬氨酸氨裂解酶(methylaspartate ammonia lyase, EC 4.3.1.2),也与肠癌宏基因组高度相关(SMD = 0.45,q < 0.1)。而L-组氨酸生物合成通路则相反(SMD = -0.33,q < 0.1)。这些结果提示,肠道微生物可能在肿瘤微环境中对氨的调节发挥潜在作用。已知肿瘤微环境中的高氨水平可导致T细胞耗竭,而本研究揭示了肠道微生物可能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分期与部位:肠癌微生物的“因地制宜”
肠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同阶段的微生物特征也可能随之变化。同时,肿瘤的原发位置也可能影响其微生物生态。
阶段演变:从“潜伏”到“爆发”的微生物印记
研究将样本分为早期(0-II期)和晚期(III-IV期)肠癌,并分别与健康对照组和腺瘤组进行比较。
早期区分能力:在区分健康个体、腺瘤患者与早期或晚期肠癌患者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曲线下面积(AUC)。例如,将II期肠癌与健康对照组区分开来的平均AUC高达0.88,而将IV期肠癌与健康对照组区分开来的平均AUC也达到了0.86。将腺瘤与健康对照组区分开来的平均AUC在0.7到0.81之间。这些高AUC值证实了微生物组在疾病早期即可展现出区分能力。
阶段内差异:单个阶段之间也部分可区分,例如I期肠癌与II期或IV期肠癌的AUC分别为0.65和0.71。
晚期肠癌的特有SGBs:研究发现17种SGBs与晚期肠癌相关,而早期肠癌仅有4种SGBs富集。其中有5种口腔来源的SGBs在晚期肠癌中显著富集,包括窄食懒惰菌(Slackia exigua SGB14784)、微小口杆菌(P. micra SGB6653)、Solobacterium SGB6833、肺炎戴氏菌(Dialister pneumosintes SGB5842)和变异链球菌(Streptococcus mutans SGB8000)。有趣的是,微小口杆菌(P. micra SGB6653)和Morbilliform格姆氏菌(G. morbillorum SGB7295)在I期肠癌中就已开始增加,而具核梭杆菌SGB6007则从II期肠癌开始持续增加并保持高丰度。这表明,这些阶段特异性的分类群通常是整个肠癌(而非健康状态)特征的一部分,微生物趋势在各个阶段呈现出连续性,而非截然不同的配置。
IV期肠癌的显著特征:在IV期肠癌中,有9种SGBs显著增加,其中哈氏亨氏菌(H. hathewayi SGB4741)表现出最大的丰度增加,而史氏甲烷短杆菌(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 SGB714)也位列高度相关物种之中。
通路的变化:研究发现早期与晚期肠癌之间有4条代谢通路存在差异(P < 0.01),而有14条通路在IV期肠癌中增加。研究再次确认了甲烷代谢(methane metabolism)与IV期肠癌之间的关联(SMD = 0.4,P < 0.01)。
左右之争:肿瘤位置决定微生物“偏好”?
除了分期,肿瘤的原发位置也对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产生影响。
粪便宏基因组差异:研究发现,基于肿瘤位置的粪便宏基因组差异也十分明显,通过所有SGBs进行分类时,模型在区分右侧结肠癌和左侧结肠癌时,平均曲线下面积(AUC)达到了0.66。即使仅使用口腔来源的SGBs,AUC仍能达到0.6。这强调了微生物组成在肿瘤位置上的差异,可能与侧特异性机制模型相关。
口腔典型菌的侧向偏好:在61种肿瘤位置差异性SGBs中(q < 0.1),有三种口腔典型SGBs在右侧结肠癌中显著增加,它们是微小类杆菌(Veillonella parvula SGB6939)、非典型魏荣氏菌(Veillonella atypica SGB6936)和化脓性真杆菌(Trueperella pyogenes SGB17137)。此外,与右侧结肠癌相关的10种SGBs中,有7种是非口腔来源的SGBs,例如链球菌属副血链球菌(Streptococcus parasanguinis SGB8071),该菌被证明能与魏荣氏菌属(Veillonella spp.)形成生物膜,这表明此类相互作用可能更是右侧结肠癌的特征。
位置与阶段的交叉: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SGBs在肿瘤位置和肠癌分期的特征中同时出现。例如,克氏肠球菌属NSJ_44(Christensenellaceae NSJ_44)和微小口杆菌(P. micra)在早期与晚期阶段差异中存在,而梭菌属SGB15390、马赛P3244梭菌(Clostridium sp. Marseille P3244 SGB29302)和GB45495 SGB63167在非转移性与转移性肠癌差异中存在。这进一步巩固了“肿瘤原发位置是影响肠癌患者肠道微生物改变的微妙但可检测的因素”这一观点。
菌株细分:微生物世界的“个体差异”
除了物种层面和功能层面,这项研究还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究了肠道微生物群落在菌株水平上的差异,以及它们与肠癌状态和分期的关联。
基因携带:菌株的“功能基因库”
研究评估了179种SGBs中基因家族(gene family, UniRef90s)的携带情况,发现尽管其中62种细菌在不同癌症状态下通常没有显著的丰度差异,但它们的菌株却在至少一个基因家族的携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广义线性模型GLM校正q值<0.05,绝对系数估计值>1)。这揭示了菌株内部存在着功能上的“个体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在肠癌中被选择或发挥作用。
菌株功能的多样性:许多含有最多基因差异菌株的物种,被识别为非口腔来源的肠癌相关物种,包括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大肠杆菌(E. coli)、脆弱拟杆菌(B. fragilis)和哈氏亨氏菌(H. hathewayi)。在20种具有最高基因携带差异的物种中,有9种同时在肠癌和对照组中富集基因,这突显了菌株层面功能差异的重要性。
SOS反应与DNA损伤:在肠癌相关的微生物中,许多分子功能发生了改变。例如,SOS反应(SOS response),一个广泛的细胞DNA损伤响应机制,在马链球菌(Streptococcus equinus)菌株中更频繁地编码。丁氏泰泽菌(Tyzzerella nexilis)和病毒丁酸单胞菌(Butyricimonas virosa)的基因家族也被预测与SOS反应相关,并在肠癌中显示出差异携带。
代谢相关基因:与群落整体结果一致,研究发现琥珀酸脱氢酶(succinate dehydrogenase)活性在粪便副苏氏菌(Parasutterella excrementihominis)菌株中编码更多,这与该脂肪酸在肠癌相关生态系统中更容易获得的假说相符。
争议性基因的菌株视角:尽管大肠杆菌素(colibactin)生产基因(来自产大肠杆菌素的大肠杆菌pks+ E. coli)和脆弱拟杆菌毒素(fragilysin)基因在物种层面没有显著富集,但研究发现它们在肠癌中携带率增加。这可能暗示了这些基因的作用可能受到特定菌株、激活条件或仅影响少数肠癌病例的影响。
氨生产的微生物贡献:碳氮裂解酶(carbon-nitrogen lyase)的基因携带情况也备受关注,因为这类基因产物会产生氨。研究识别出五种在肠癌生态系统中编码产氨相关基因的细菌,包括产酸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 oxytoca)、内脏嗅杆菌(Odoribacter splanchnicus)、肠道拟杆菌(Bacteroides intestinalis)、粪便副苏氏菌(Parasutterella excrementihominis)和艰难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其中,精氨酸琥珀酸裂解酶(argininosuccinate lyase)基因由粪便副苏氏菌携带,而氨是其已知的分子产物。
谱系分化:隐藏在“家族树”里的秘密
研究进一步通过菌株水平的系统发育模型(phylogenetic model)分析,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落中菌株分化与肠癌的关联。
显著的菌株分化:研究识别出多个物种,它们在不同的系统发育谱系中携带优势菌株,并且这些菌株的携带与肠癌显著相关。共有8个物种在广泛定义的肠癌(0-IV期)中表现出菌株层面的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菌株层面的关联,许多都是独立于物种水平丰度变化的,这意味着即使物种总数没有显著改变,但其内部的菌株构成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疾病。
特定菌株与肠癌关联:例如,嗜黏蛋白菌(Lachnospira eligens,以前称为Eubacterium eligens)和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 rectale)的菌株系统发育谱系在肠癌中呈现差异。尽管直肠真杆菌之前被认为其遗传差异与地理起源相关,但本研究在控制了地域因素后仍然发现了这种菌株差异,表明其在肠癌中存在更深层次的遗传分化。
晚期肠癌的菌株特征:菌株谱系分析最强的信号出现在早期与晚期肠癌,以及转移性与非转移性肠癌的区分中。所有被识别出与早期或晚期肠癌相关的物种,在转移性与非转移性比较中也同样存在,这可能表明IV期肠癌是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双环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和粪便梭菌(Clostridium fessum)的亚类与晚期肠癌(III-IV期)密切相关。特别是,双环瘤胃球菌(R. bicirculans)的菌株在晚期肠癌患者中,其碳水化合物代谢相关基因的携带率更高。已知碳水化合物代谢的改变与肿瘤分化有关,这提示了双环瘤胃球菌可能通过其特定的代谢途径,促进肿瘤的进展。
肠道微生物,照亮抗癌之路
这项对3,741份粪便宏基因组样本的里程碑式分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分辨率,深刻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落与结直肠癌的复杂关系。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基于粪便微生物的肠癌筛查模型,显著提高了预测准确性,更深入到菌株水平,描绘出了一幅更为精细的微生物图谱。
主要发现的价值与启示:
更精准的早期筛查:研究证实了肠道宏基因组学在肠癌筛查中的巨大潜力,平均曲线下面积(AUC)达到0.85,这为开发无创、高效的早期诊断工具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口腔微生物的“罪魁祸首”:研究再次强调了口腔典型微生物在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它们可能通过渗入肠道,并在肿瘤微环境中形成生物膜,甚至影响肿瘤位置的特异性。这为肠癌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例如通过改善口腔健康或靶向清除肠道中的口腔病原菌。
疾病进展的微生物“时间轴”:研究首次系统地描绘了肠道微生物群落从腺瘤到不同肠癌分期(早期、晚期、转移性)的变化趋势,揭示了某些特定菌种和菌株在疾病进展中的动态角色,如微小口杆菌在早期就开始增加,而哈氏亨氏菌和史氏甲烷短杆菌在晚期肠癌中显著富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疾病的分子机制,并为不同阶段的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菌株层面的“细致入微”:这项研究的突破性在于深入到菌株层面,揭示了即使在物种丰度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特定菌株的基因携带差异也能与肠癌相关。例如,双环瘤胃球菌和粪便梭菌的亚类与晚期肠癌密切相关,且双环瘤胃球菌在晚期肠癌中携带更多碳水化合物代谢相关基因。这为未来的精准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菌种”,更是“菌株”以及它们独特的功能属性。
功能机制的深度挖掘:研究不仅识别了与肠癌相关的特定微生物物种,更深入分析了其功能变化,如产硫酶、油酸生产和氨代谢等。特别是肠道微生物在氨调节中的潜在作用,为理解肠癌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未来可能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来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的效果。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一项以关联性(association-based)为主的研究,它无法直接证明肠道微生物与肠癌进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将需要更深入的机制探索,例如通过动物模型、体外实验和人体干预研究,来验证这些微生物生物标志物的因果作用。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的成果无疑是肠道微生物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它不仅为肠癌的无创筛查和早期诊断提供了更强大的生物标志物,更从组成和功能层面,以及前所未有的菌株分辨率,刻画了疾病进展中肠道微生物的特征。未来,随着更多大型、多样化队列研究的开展,以及更先进分析工具的开发,我们有望将这些微生物“侦探”真正带入临床,为结直肠癌的精准预防、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照亮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共同期待,肠道微生物这个微观世界,能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多宏大的希望!
(来源:生物探索)
原文出处:Piccinno G, Thompson KN, Manghi P, Ghazi AR, Thomas AM, Blanco-Míguez A, Asnicar F, Mladenovic K, Pinto F, Armanini F, Punčochář M, Piperni E, Heidrich V, Fackelmann G, Ferrero G, Tarallo S, Nguyen LH, Yan Y, Keles NA, Tuna BG, Vymetalkova V, Trompetto M, Liska V, Hucl T, Vodicka P, Bencsiková B, Čarnogurská M, Popovici V, Marmorino F, Cremolini C, Pardini B, Cordero F, Song M, Chan AT, Derosa L, Zitvogel L, Huttenhower C, Naccarati A, Budinska E, Segata N. Pooled analysis of 3,741 stool metagenomes from 18 cohorts for cross-stage and strain-level reproducible microbial biomarkers of colorectal cancer. Nat Med. 2025 Jun 3. doi: 10.1038/s41591-025-03693-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46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