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学术热点追踪
Nature | 肠道“造物”,血管“遭殃”:研究揭示血脂不高,血管为何还会堵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如同悬在全球健康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当之无愧的头号杀手。而在这背后,一个共同的“幕后黑手”常常在默默作祟,那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想象一下,我们体内的血管如同城市的供水管道,动脉粥样硬化则像是管道内壁逐渐积累的水垢和锈迹。这些由脂肪、胆固醇、钙和其他物质组成的斑块 (plaque) 会让血管变窄、变硬,最终可能导致管道堵塞,引发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多年来,我们对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策略主要集中在管理那些“经典”的风险因素上,比如降低“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控制血压和血糖。然而,一个棘手的现实摆在眼前:许多看似健康、风险评分不高的人,血管内早已悄然发生病变;而即便是接受了最佳治疗的患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面临心血管事件的“残余风险” (residual risk)。这表明,在胆固醇之外,一定还有其他未知的“点火器”在推动着疾病的进程。近年来,研究人员的目光开始投向我们的肠道。这个栖居着数万亿微生物的“隐秘器官”——肠道菌群 (gut microbiome),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最近,一篇发表在《Nature》上的重磅研究“Imidazole propionate is a driv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atherosclerosis”,就成功“破译”了这样一段危险的“密语”。研究人员发现,一种由肠道微生物产生的名为咪唑丙酸 (Imidazole propionate, ImP) 的代谢物,不仅仅是疾病的“旁观者”,更是直接驱动动脉粥样硬化的“肇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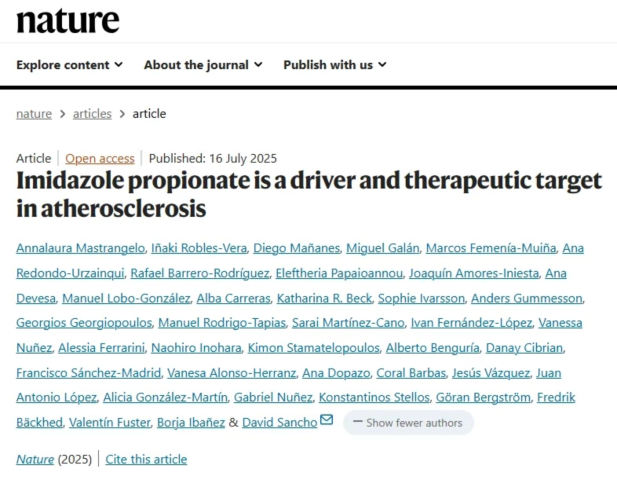
茫茫分子之海的“第一现场”:一桩巧妙的实验揪出嫌疑物ImP
要在一个拥有成千上万种分子的复杂生物体内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亚于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名特定的嫌疑人。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动物实验,如同侦探办案一般,层层筛选,最终锁定了目标。
他们首先请出了动脉粥样硬化研究领域的“功勋模型”——一种名为ApoE基因敲除 (Apoe-/-) 的小鼠。这种小鼠天生容易患上动脉粥样硬化,是模拟人类疾病的理想工具。研究人员将这些小鼠分成了几组,喂食不同的“外卖”:普通鼠粮、高胆固醇饲料 (High-cholesterol, HC)以及高胆固醇高胆碱饲料 (HC/HC)。
正如预期的那样,连续8周的“垃圾食品”喂养让小鼠的血管很受伤。通过油红O染色 (Oil Red O staining)——一种能让脂质斑块现出红色的技术,研究人员清晰地看到,与几乎没有斑块的健康餐组相比,垃圾食品组小鼠的主动脉弓上布满了红色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斑块面积覆盖率达到了约15%。
接下来,是揭示肠道菌群角色的关键一步。研究人员在部分小鼠的饮用水中加入了“广谱抗生素鸡尾酒” (antibiotic cocktail)。抗生素会无差别地“清扫”肠道内的大部分微生物。结果令人振奋:在同样吃着“垃圾食品”的情况下,接受了抗生素治疗的小鼠,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为肠道菌群直接参与疾病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除了菌群,疾病就减轻了。
既然菌群是“同谋”,那么它们作案的“凶器”是什么呢?为了从血液中成千上万的代谢物中找出这个“凶器”,研究人员动用了非靶向代谢组学 (untargeted metabolomics)。这就像对血液进行一次无差别的、地毯式的搜查,分析所有小分子物质的种类和含量的变化。
分析结果一目了然。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LS-DA) 图上,代表不同组别小鼠的样本点根据其整体代谢谱的差异,自动地“抱团”分开。这说明,不同的饮食和肠道菌群状态,确实导致了血液中代谢物图谱的巨大变化。
在这次大规模的“排查”中,一个此前在动脉粥样硬化领域并不出名、但与菌群代谢密切相关的分子脱颖而出,它就是咪唑丙酸 (ImP)。研究数据显示,血浆中ImP的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呈现出惊人的正相关性。斑块越大的小鼠,血液中的ImP水平就越高。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 (Spearman's rank-order correlation),二者的相关系数 (r) 高达0.73,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关联信号。
进一步分析肠道内容物的16S rDNA测序数据,研究人员还找到了ImP水平与特定菌群丰度的关联。例如,ImP的水平与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 (Escherichia-Shigella) 的相对丰度呈正相关,而与一些被认为可能是有益的菌属如月形单胞菌属 (Selenomonas) 呈负相关。
至此,第一阶段的“侦查”宣告结束。在小鼠模型中,一个由肠道菌群产生、并与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紧密相关的“头号嫌疑物”——ImP,已经被成功锁定。但这仅仅是开始,它在真实世界的人类身上,是否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呢?
从实验室到真实世界:ImP对人类同样是威胁吗?
为了探究ImP是否同样是人类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标志,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两个大规模的人群队列研究。
第一个是著名的PESA队列 (Progression of Early Subclinical Atherosclerosis study)。这项研究招募了400名年龄在40至54岁之间、无心血管疾病症状的健康银行职员。研究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先进的2D/3D血管超声和CT扫描技术,去“偷窥”这些健康人血管的真实状况。结果发现,许多人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血管壁上已经出现了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 (subclinical atherosclerosis)——即没有引起任何症状的早期、沉默的斑块。
研究人员测量了这400名志愿者血浆中的ImP水平,结果与小鼠实验高度一致:体内存在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个体,其血浆ImP浓度显著高于血管完全健康的对照组。例如,在PESA队列中,健康对照组的ImP中位浓度约为10 nM,而在有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个体中,这一数值上升到了约15 nM。
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了清晰的“剂量-反应关系”。随着血浆ImP浓度的升高,个体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也随之攀升。为了进一步确认,研究人员在另一个独立的、规模更大的IGT队列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cohort) 中重复了这项检测,结果再次证实了PESA队列的发现:ImP水平升高与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之间存在着稳固的关联。
如果ImP只是一个孤立的标志物,它的意义或许有限。但研究人员发现,ImP与一系列传统的心血管风险因素“同流合污”。相关性分析显示,ImP水平与空腹血糖、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体重指数 (BMI)、内脏脂肪、血压等指标均呈正相关,而与“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HDL) 呈负相关。这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ImP升高,往往伴随着一个整体不健康的代谢环境。
然而,研究人员并未止步于此。他们想知道,ImP是否能区分出那些更“危险”的斑块?利用一种名为18F-FDG PET/MRI的先进影像技术,研究人员可以识别出那些正在发炎的“活性”动脉粥样硬化 (active atherosclerosis)。这是该研究在人类研究部分最关键的发现之一:与拥有非活性(稳定)斑块的个体相比,那些体内存在活性、发炎斑块的个体,其血浆ImP水平要高得多!例如,在FDG阳性(有活性病变)组中,ImP的中位浓度显著升高至约20 nM,远高于FDG阴性(无活性病变)组。这说明,ImP不仅能提示“有没有”斑块,更能反映斑块“危不危险”。
最有力的一项证据来自多变量回归分析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研究人员将所有传统风险因素,如年龄、性别、吸烟、血压、血脂、血糖等全部纳入模型进行校正后发现,高水平的ImP仍然是预测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活性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意味着,ImP所提供的信息,是传统指标无法完全覆盖的。它不是其他风险因素的简单“回声”,而是一个独特的、新增的风险信号。
“钓鱼执法”:证实ImP是肇事者,而非旁观者
为了证实ImP是真正的“肇事者”,研究人员进行了一场巧妙的“钓鱼执法”实验,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主动给动物ImP,它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吗?
这次,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动脉粥样硬化易感小鼠——Ldlr基因敲除 (Ldlr-/-) 小鼠,并让它们只吃健康的普通鼠粮。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小鼠的血管应该保持光洁。然后,实验的“神来之笔”出现了:研究人员在这些小鼠的日常饮用水中加入了ImP。
仅仅12周后,这些本不该生病的小鼠,它们的主动脉上竟然出现了清晰可见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病变面积从接近0%增加到了约4%。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一过程完全独立于传统的风险因素——在整个实验期间,这些小鼠的血浆总胆固醇和血糖水平与未接受ImP的对照组相比,没有任何变化。这铁一般的事实证明,ImP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绕开高血脂这条“经典路径”,直接在血管壁上“点火”。
那么,ImP在体内究竟做了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它发动了一场全身性的“免疫风暴”。血液检测显示,接受ImP的小鼠体内,多种促炎性免疫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包括以Ly6C hi为标志的“冲锋队”单核细胞 (monocytes),以及被称为“战争贩子”的TH1和TH17辅助性T细胞 (T helper cells)。这些细胞都是公认的动脉粥样硬化病理过程中的关键驱动者。
为了探究血管壁局部发生了什么,研究人员动用了单细胞RNA测序 (scRNA-seq) 技术,这项技术能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读取”主动脉组织中每一个细胞的“工作状态”。结果显示,ImP不仅让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增多,还诱导它们大量“渗透”到主动脉壁内。更重要的是,ImP直接“激活”了血管壁原有的细胞,让它们纷纷开启了与炎症、免疫应答相关的基因程序。
既然免疫系统被调动了起来,那么它是否是ImP“作案”所必需的“武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精巧的骨髓移植实验。他们使用了Rag1基因敲除小鼠,这种小鼠先天缺乏成熟的T细胞和B细胞。结果,这些“免疫缺陷”小鼠,对ImP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出了显著的抵抗力。这有力地证明了,适应性免疫系统是ImP发挥其促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关键媒介。
顺着这条线索,研究人员继续深挖,通过磷酸化蛋白质组学分析,他们发现ImP处理过的细胞中,mTOR的信号通路 (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 signaling pathway) 被显著激活了。为了证实mTOR通路的关键作用,研究人员再次运用了基因工程手段,构建了一种在髓系细胞中特异性敲除mTOR通路关键蛋白Raptor的小鼠 (Lyz2ΔRaptor)。当给这些“mTOR开关失灵”的小鼠喂食ImP时,它们同样被保护了,不再发生动脉粥样硬化。
至此,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被完整地描绘出来:肠道菌群产生的ImP进入血液,作用于髓系免疫细胞,激活了其内部的mTOR信号通路,进而引发了全身和血管局部的炎症反应,最终驱动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破解“通讯密码”:细胞如何“听懂”肠道菌群的信号?
如果说ImP是肠道菌群发出的一个“信号分子”,那么我们的细胞上必然有一个对应的“接收器”或“天线”来识别它。破解这个“通讯密码”,是理解ImP作用机制并开发靶向疗法的关键。
研究人员注意到,ImP的分子结构中包含一个“咪唑环” (imidazole ring)。基于这一化学特征,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ImP可能是通过咪唑啉受体 (imidazoline receptor, IR) 来发挥作用的。在众多咪唑啉受体中,I1受体 (I1R)——其蛋白实体也被称为Nischarin (Nisch)——成为了首要怀疑对象。
一系列体外细胞实验迅速验证了这一猜想。当研究人员在用ImP处理巨噬细胞的同时,加入一种名为AGN192403的I1R特异性拮抗剂(即受体阻断剂)时,ImP的促炎作用被完全“静音”了。无论是在mTOR通路的激活水平上,还是在炎症因子的分泌上,AGN192403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抑制效果。
基因层面的证据则更为直接。研究人员利用小干扰RNA (siRNA) 技术,在细胞中暂时“沉默”了编码I1R的Nisch基因。这些对ImP信号变得“耳聋”的细胞,即使在ImP存在的情况下,也无法被激活。这表明ImP正是通过I1R这个特定的受体来传递其炎症信号的。
最终的决断性证据,依然来自动物模型。研究人员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嵌合体”小鼠——只在髓系细胞中特异性地敲除了I1R受体 (Lyz2ΔNisch)。这意味着,这些小鼠全身其他细胞的I1R功能完好,唯独关键的免疫细胞“失聪”了。
当给这些“髓系I1R失聪”的小鼠喂食ImP时,奇迹发生了:它们对ImP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表现出完全的抵抗力!尽管血液中同样充满了高浓度的ImP,但由于免疫细胞上的“天线”被拆除了,这个危险信号无法被接收,后续的炎症瀑布也就无从发起,血管因此得到了完美的保护。这项实验将整个故事串联了起来:ImP通过与髓系细胞表面的I1R受体结合,从而驱动动脉粥样硬化。
新疗法的曙光:从源头阻断,而非仅控制胆固醇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治疗性干预都还局限于ImP诱导的、相对“非主流”的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一个更具临床意义的问题是:这种新的阻断策略,能否对抗由高胆固醇这一“主流”原因引起的、已经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
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最接近临床情境的动物实验。他们给ApoE-/-小鼠喂食高胆固醇饲料(HC diet),让它们先患上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在斑块形成4周后,他们开始对其中一半的小鼠进行治疗,在饲料中加入I1R阻断剂AGN192403,持续4周。这完美地模拟了对一个已经确诊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进行药物干预的过程。
治疗结果令人鼓舞。与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相比,使用AGN192403治疗的小鼠,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被有效遏制,斑块面积显著减小。例如,在雄性小鼠中,治疗组的主动脉病变面积中位数仅为对照组的一半左右。
更深入的组织学分析揭示了更重要的变化。AGN192403不仅减小了斑块的“尺寸”,还改善了斑块的“质量”。治疗显著减少了斑块内部危险的坏死核心 (necrotic core) 的面积,并降低了细胞凋亡的水平。这意味着,这种疗法可能使斑块从“易碎、危险”的状态,变得更“稳定、安全”,从而降低斑块破裂的风险。
最关键的一点再次得到验证:所有这些保护效果,都是在不影响小鼠血浆总胆固醇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这证明了,阻断ImP-I1R轴是一种全新的、独立于降脂通路的动脉粥样硬化干预策略。它直接靶向了疾病的另一个核心驱动力——炎症。
这项实验描绘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一种新型药物,能够通过阻断来自肠道菌群的有害信号,直接抑制血管炎症,稳定动脉斑块,并且可以与现有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协同作战,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夹击动脉粥样硬化,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残余风险”的难题。
这项发现,对你我意味着什么?
这项从分子、细胞、动物到人队列的系统性研究,如同一部精彩的科学侦探剧,为我们完整地讲述了ImP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可能深刻地改变我们未来对心血管疾病的认知和防治模式。
首先,它可能带来全新的诊断工具。
目前的风险评估过度依赖胆固醇等传统指标,但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来自肠道菌群的ImP,尤其是它与“活性”动脉粥样硬化的强关联,可能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未来,一次简单的血液检测,或许就能通过ImP的水平,帮助医生识别出那些传统方法会漏掉的、处于疾病极早期或拥有高风险炎性斑块的“隐形”患者。它可以作为他汀类药物治疗的“伴随诊断 (companion diagnostic)”,评估患者的炎症残余风险,并指导是否需要启动抗炎治疗。
其次,它开辟了全新的治疗途径。
这项研究最令人兴奋的部分,莫过于它揭示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靶点——ImP-I1R轴。这意味着,针对I1R受体的拮抗剂,有望被开发成一类全新的心血管药物。它们不以降脂为目标,而是直接作用于炎症这一疾病的根本驱动力之一。这样的药物一旦问世,将与他汀类药物形成完美的“黄金搭档”,分别把控“血脂”和“炎症”两个关口,为患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双重保护。
最后,它将个性化医疗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项工作再次凸显了我们与体内共生微生物之间那种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关系。它告诉我们,我们吃下的食物,经过肠道菌群这个“中间加工厂”的处理,可以产生直接影响我们血管健康的信号分子。这为基于饮食和肠道菌群的个性化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年度体检报告上,除了血脂、血糖,或许还会有一个“肠道代谢物”报告。医生可能会根据你的ImP水平,为你量身定制饮食建议,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心血管疾病。
总而言之,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让我们聆听并破译了一段来自我们体内最深处——肠道菌群——的“密语”。它告诉我们,健康的血管,不仅关乎我们自身的基因和生活方式,也关乎我们如何“款待”那数万亿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伙伴。在这场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漫长战争中,我们终于在胆固醇这条主战线之外,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充满希望的“第二战场”。而这,或许正是我们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所在。
(来源:生物探索)
原文出处:Mastrangelo A, Robles-Vera I, Mañanes D, Galán M, Femenía-Muiña M, Redondo-Urzainqui A, Barrero-Rodríguez R, Papaioannou E, Amores-Iniesta J, Devesa A, Lobo-González M, Carreras A, Beck KR, Ivarsson S, Gummesson A, Georgiopoulos G, Rodrigo-Tapias M, Martínez-Cano S, Fernández-López I, Nuñez V, Ferrarini A, Inohara N, Stamatelopoulos K, Benguría A, Cibrian D, Sánchez-Madrid F, Alonso-Herranz V, Dopazo A, Barbas C, Vázquez J, López JA, González-Martín A, Nuñez G, Stellos K, Bergström G, Bäckhed F, Fuster V, Ibañez B, Sancho D. Imidazole propionate is a driv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atherosclerosis. Nature. 2025 Jul 16. doi: 10.1038/s41586-025-09263-w.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670786.
